![]() 当前位置: 绵竹市 > 绵竹市旅游 > 关于那些无用而美好的事物
当前位置: 绵竹市 > 绵竹市旅游 > 关于那些无用而美好的事物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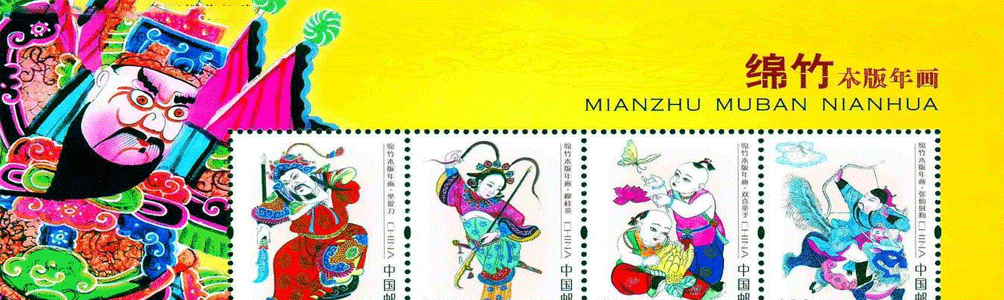
![]() 当前位置: 绵竹市 > 绵竹市旅游 > 关于那些无用而美好的事物
当前位置: 绵竹市 > 绵竹市旅游 > 关于那些无用而美好的事物
我们所处的时代
为什么要说博物学这件事情?博物学为什么会衰落?这与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有关。对这样的时代有不同的描写,有人说朝气蓬勃、轰轰烈烈,也可以说“现在是豁出生命搞发展”。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,对这个时代评价不一样,有人说好得很,有人说糟得很,“轰轰烈烈”作为表象大概是一个基本事实。
这样一个时代是日益科技化的时代,“科”字在此并不根本,重要的是“技”。这个时代日益技术化、日益人工化。科学技术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,但是,作为一种高智商智力活动的科学技术,越来越远离了公众。公众很难理解科学家在做什么?科学家做成的成果,有些百姓已在普遍使用,能够理解,但相当一部分根本理解不了,也是很难普及的。可以设想,没有学过高等数学的人,怎么能够理解理论物理学的前沿,那是不可能的。能够理解量子力学的很少,但是很多人声称能够理解,霍金的《时间简史》很受欢迎,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懂得呢?很难说。
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科技创新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,但是有一点需要非常明确,科技创新并非首先从公众的需求出发,而是从资本增值和权力控制这个角度出发。这个不用特别论证,稍想一下就明白了。比如我们在座的各位使用的电脑,软硬件在不断地升级,实际上不需要升的那么频繁,可是如果频繁升级,厂家就没有那么多钱可赚。许多国家开展军备竞赛,并不是老百姓喜欢打仗,是军火商喜欢打仗,还有其他利益集团。
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,科技成为这个时代的火车头,是个动力装置,它拖动着整个社会加速前行。我们绝大多数人甚至都觉得科技推动的力量还不够,希望科技加大力量,推动我们的世界更快速地前进,向哪前进呢?开车的人都有个经验,当车开得很快的时候,它的风险也在增加。但是我们乘坐在现代化这辆列车上,希望它开得越来越快,这意味着什么?当然它有好的方面,有人喜欢快,就像坐过山车一样,有人希望一直坐过山车。多数公众现在被迫玩着一种有智力无智慧的游戏。绝大多数人实际上是被绑架,想玩不想玩,都要跟着玩。实在不想玩的可以下车,怎么下车呢?就是跳车。跳车的后果大家是知道的,要么捽伤,要么被这个时代所抛弃,这就是现代性的逻辑。这个逻辑好不好呢?成功者都认为很好,失败者认为不好,还有大部分是中间者。
这样的时代给我们直接的感受,就是社会的步伐特别快,越来越快,不确定性在增长。虽然我们的收入增加了一部分,但是因为不确定性增加,两个东西互相抵消了。我们在生活中感觉到越来越忙,今天比昨天忙,明天比今天还要忙,我们活着似乎就是为了忙?我想年纪大的人会有这种感觉,二十多岁的人希望越忙越好还可以理解。忙是有代价的,我们在“挖掘”大自然、破坏大自然、掠夺我们后代的利益,在以破坏可持续性发展为代价。
在这样一个时代,我们这代人大概已经做得差不多了,但是还没有善罢甘休,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上,让我们的孩子做好激烈竞争的准备:“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。但是这样想和做的后果是什么?它剥夺了孩子的童年!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有快乐的童年,但是现在的学生没有这种童年。很多学生都是“小老样儿”,从小就说大人的话,就做大人所做的习题。比如上各种班:奥数班、钢琴班、英语班,要争取成为人上人。没有明说的想法是:准备战胜你的同桌、战胜你的同学、战胜你的同事、战胜你的同胞。我们的各级教育,是真的培养人才?还是想战胜你的同桌呢?很大程度是后者。我们的学制一再延长,用我的话来讲,人生的大好时光,相当程度上浪费在课堂中。人生最黄金的时光在二十多岁,我们现在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博士,要读二十多年,大部分时光都在学习课本知识,学习竞争的技巧,知识是学不完的。等博士毕业以后,好象有点知识了,突然发现,我们的知识大部分没用,还要继续学习。只有人类这个物种如此,没有其他物种象人这样刻苦学习。有多少人想过:我们为什么要刻苦学习呢?是否天经地义地认为不学习就不是人了,我们人的优越性似乎就在于学习。但是辩证地看,人的负担太重了,猴子、老虎、昆虫等虽然也学习,但都没有这么大的负担,我们人号称是有理性的动物,理性在于算计、在于精确地计算,但是就知识的积累这方面来说,我们的“理性”在什么地方呢?没有简单的答案,我只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。
如果我们对这样一些问题进行思索,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考虑,我们需要过怎样的人生,我们人类想干什么?我们怎么样与周围的世界相处?进一步考虑,在现代社会中,起着拖动作用的火车头:科技,它到底是什么?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,生产力一定就是好的吗?生产力在某种程度它也是破坏力。
百姓自己的博物学
第一,博物学有悠久的历史,它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传统。
博物学与自然科学有关,但是它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。目前博物学中的一部分可算作自然科学,但大部分不能算。
博物学曾是自然科学中的一个传统,现在已经衰落。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衰落的、被抛弃的这门学问,它也许还有恢复的必要。
自然科学有四个传统。这四个传统是我概括的,未必有道理,大家可以听听。这四个传统是博物传统、数理传统、控制实验传统、数字模拟传统。
最早出现的就是博物传统。在近代科学诞生以前很久很久,就有博物传统。近代科学经历的时间是很短的,三百多年,从伽利略到现在也就三百多年,而博物学起码有几千年。年相对于人类历史而言是极短的时间,人们要学会从不同尺度上特别是更大的尺度上看各种知识的积累!近代科学革命通常被说成是数理科学革命,伽利略、牛顿引发的这场革命主要在天文学、力学方面,再扩大一点就是数理科学的革命。这场革命使得科学的精神照亮了整个世界,也结束了中世纪的统治。数理传统从此大力发展,到现在几乎变成了一枝独秀,把博物学传统压了下去。这只是宏观地讲,在十九世纪的时候,博物学传统还比较昌盛,比如赖尔、达尔文、华莱士等都是优秀的博物学家。到了二十世纪,博物学就越来越衰弱了,很难找到非常杰出的博物学家。当然也有,比如研究蚂蚁的专家E.O.威尔逊,他是优秀的博物学家。
第三个传统叫控制实验传统,它与数理科学传统差不多同时诞生的。它在做控制实验,控制实验和我们平常的简单实验不一样。它主要是在实验室中模拟大自然,把现实中多个变量控制起来,只考虑一个变量或者几个变量的变化时系统可能产生的结果。总之是约束多数的参量,只考察少数几个变量的变化来看这个系统有什么样的效果,以此来解释大自然、改造大自然。弗朗西斯·培根对这种实验传统很早就进行过呐喊,但他本人不是科学家,他只是在方法论上来鼓吹经验科学、实验方法。当今世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主要工作都属于控制实验这个传统。
数理和控制实验合起来,非常有效,也加强了人们对机械论、还原论的信念。还原论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,也涉及到人们对世界的看法,这里不细讲。
进入到二十世纪,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,数值模拟传统突然崛起,这是与计算机联系在一起的。现在如果进行一个核爆炸,可能不会直接引燃一枚核弹,通常是在计算机上做数字模拟。象火箭发射、化学药品的合成等等,也是要先做数字模拟,这非常有效,可以节约很多钱财。这个传统非常新,将来也会发展的越来越好。
这样的四大传统是否就把整个自然科学都概括无遗呢?不可能。它们是主要的几个方面,这四大传统是按时间先后产生的。它们不是独立的,是人为抽象出来的,仅仅是MaxWeber所说的“理想类型”而已。它们是为了说明、理解方便而人为概括出来的类型。现实的自然科学要比这复杂得多。可能的情况是:博物传统与数理传统结合在一起,数理与控制实验结合在一起,或者控制实验与数字模拟结合在一起。有多种组合,各有所侧重。现在讲博物学,也不等于不要数学、不要实验。
四大传统中,最肤浅的、最古老的、现在看来最不重要的,就是博物学传统。前面提过,不重要的程度可用现在各级学校中已经不讲授它了来衡量。人们认为它没有用。但是真的没有用吗?我们后面会看到,某种程度上它还是有用的,它有存在的必要。我们要争取的,不是博物学全能,不是博物学一花独秀,根本不是这样。我们主张的只是最低纲领:要求博物学的生存权。但即使这样,也可能触犯别人、别的领域的利益。
第二,博物学距离“生活世界”最近,修炼博物学可以增加普通人对世界的感知能力。
我是学哲学的,稍提一下哲学上的“生活世界”。我本科学的是地质学,后来改学哲学了。哲学上现在有一派叫现象学。PPT这一页这有两位现象学的大师,左边这一位是胡塞尔,右边这位是梅洛庞蒂。现象学家提出一个想法,和我们日常的想法不同,几乎是颠倒过来的。他们认为:现代科学所描述的世界,现代科学所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,不是第一位的,而是第二位的。再直白一点,科学告诉我们的东西是“次要的”,这话不能曲解为不重视科学。现象学家是非常重视科学的,正因为重视科学他们才提出这样一个想法。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普通百姓主观的“生活世界”而不是客观的“科学世界”。注意,我们可能从小就听惯了:主观是不好的,客观才是好的。但在现象学中不是这样。
在现象学家看来,更靠谱儿的是普通人每天所经历到的、感受到的东西,不是自然科学家所描述的东西。比如我们每天能够感到冷热、风寒、软硬、亮暗、香臭等等,这些东西是直接知识,是我们直接体验到的,是我们的身体、肉体直接告诉我们的,是不需要反思的。言语、理论可以撒谎,肉体并不撒谎。我们任何一个人,哪怕没有受过高等教育、初等教育都明白直接呈现的感觉,虽然它们有些主观。在现象学家看来,人类个体能够切实感受到的主观的东西是第一位的、完整的、真实的,也是复杂的;相反,自然科学告诉我们的东西是第二位的、客观的、简化的、不是很真实,但很有效。自然科学告诉我们大爆炸、H7N9、原子、夸克、冠状病毒、DNA等等,这些东西是导出的知识,是构造出来的知识,是第二位的。现象学说的不一定都正确,但哲学家胡阻塞尔等也并非胡说!现象学提供了人们一个思考世界的一种新方式,它有一定的道理。
现象学这种想法与我们要恢复博物学的想法不谋而合。在科技日益发达,带领我们加速前行的过程中,我们学到的科学知识越来越多,我们越来越有本事,甚至可以毁灭地球,但是人们还是需要点别的东西的,需要什么呢?我们多数人都患有一种自然缺乏症,对大自然越来越陌生,越来越远离大自然。我们忽视自己的感觉,相比于自然科学,觉得它们不真实。
我说的大自然是广义的,包含桌子、外界物体等等,更多的还是指山川、草木、河流、天空、星象等。现代人所缺少的,就是一种悠久的博物传统,现代知识分子、高级文化人更缺少。农民反而不大缺少,为什么呢?农民知识很贫乏,但要说清楚农民的什么知识贫乏。农民直接感性知识并不贫乏,农民是了解土地的,而城里人是不了解土地的,农民对土地的知识可能比一位土壤专家了解的还要多。土壤专家了解的是可控实验那一小部分知识,比如PH值、锰元素的影响、钙的含量等等,农民虽然不知道钙是什么东西,但是他知道某种土壤适合种植什么东西。博物学是距离我们日常百姓生活最近的一门学问,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,那么修炼博物学可以使普通人对自己周围世界越来越了解,有很好的感知能力。博物学不限于人类所独有,其它动物可能某种程度也具有博物学知识。人与其他动物本来是连续过渡的,不应当截然划界。
第三,科技的高速发展,反而剥夺了普通人对世界的独立观察、感知和思考。
现代科技高度、高速发展,自然科学本来是让我们理解自然界,比如科学家告诉我们这棵树叫什么名字?这个木材含有什么元素?这种水是不是有毒,这种食材是不是有营养?科学家的话要相信,但是不能全信,为什么呢?
我举个例子,汶川地震大家可能还有印象。年5月10日《华西都市报》正式报道,四川绵竹市出现一种现象:癞蛤蟆在大规模迁徙,数十万癞蛤蟆横穿马路,有相当一些被碾死。
据报纸报导,有村民说:“这种现象是不是啥子天灾的预兆哟?”但绵竹市林业局的专家代表官方声音,解释说:这与天灾无关,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,还会为当地减少蚊虫。专家说这是正常现象,证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。事后看,林业局的专家跟村民一样也不懂。专家也没有进行过调查,但专家从科学理性出发,代表科学,代表权威发言,要安定人心。两天以后,5月12日,大地震发生,死了几十万人,说的不好听点,这就是相信科学的后果,但是整个过程中没有人指责科学。我也不是想指责科学家、林业局。我只是想提醒,林业局专家所说的东西未必可信,而村民所说的东西也未必不可信。如果我们更多地相信村民所讲的,也许会好些。村民的感觉是经验的积累,他污染经验告诉自己,这绝对是反常现象。大量的癞蛤蟆走到街道上被汽车辗得稀碎,满街的癞蛤蟆,这算正常吗?只有以某种力量武装起来的人能够理直气壮地说出“正常”这种话,科学家是敢说话的。事后大家都知道,百姓的感觉是对的,科学(家)是错的,科学家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做调查,也没有经验。其他动物有感知大自然风险的能力,而人没有;也许我们的祖先曾经有,但后来退化了。我们更相信传感器、天气预报、专家怎么说,我们自己没有判断能力,但癞蛤蟆有这种能力。我们知道大象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感知地震,大象的脚能够感受到次声波,人却不灵。蝙蝠能够利用回声定位,我们人不能。我们人的确一个很特别的动物而已,但跟其它动物比未必优秀,只是我们人自己觉得是万物之灵。
还有一个例子,科学家总是在说“地球变暖”,哪位科学家严格证明了地球在变暖呢?我也努力地在相信科学家所的地球在变暖,但是我相信不了。我原来是学地质的,在地质上考察地球演化是在上亿年的层面考察的,地球有四十多亿年的历史,地球在历史上冷暖的变化非常剧烈,没有什么明显的规律。我们怎么知道现在是变暖还是变冷呢?也许连续十年在变暖、连续一百年在变暖、连续一千年在变暖,可下一个一千年也许变冷呢?坦率说人们不知道,但是现在科学家就要求我们相信地球在变暖,地球变暖我们就要执行一系列的政策。民间有说笑话,人们感觉这几年天气确实变暖了,这证明了科学家的说法。可这几年冬天又特别寒冷,为什么寒冷呢?科学家又说也是因为地球变暖,因为变暖,所以两极的冰化了,影响了海洋和大气。以不变应万变!这种解释和伪科学解释是一样的,它打了科学的招牌,用些数据包装起来,使人们看着它觉得很科学。保护地球、“减排”是对的,是伦理上的要求,这与地球是否变暖没有必然关系。无论变暖还是变热,都没有糟蹋地球的理由。
北京几年前还发生过一件事。气象局和电视台均预告“麦莎”光临,明天北京将有建国以来最大的暴雨。为了安全起见,北京的一些水库把水放了。要知道北京是极缺水的,攒那些可不容易。但是第二天北京只下了一场毛毛雨。没有任何人出来哪怕是象征性地道歉一下。科学是可错的,科学允许出错,可错性是科学之为科学的良好标志。这是科学哲学上讲的。百姓并不懂这个。气象局和电视台为何不把话说得留有余地?
我举这些例子,是为博物学找理由、找根据,也在提醒我们,不是要贬低科学。但我的确想指出,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。科学需要传播,但必须是双向的。传统的科普道路是走不通的,《华西都市报》所报道出来的林业部门的言论,无非是从一种科普的角度来安慰百姓,告诉百姓一切都正常,没有不祥之兆。传统科普的理念是什么呢?中国科院院樊洪业先生对“传统科普”有个描述,概括了四点,我想引在这里。引他的话比较有说服力。樊先生说,传统科普是从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中延伸出来的,科普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;科普的对象定位在工农兵,后来有所扩展;科普的方针是结合生产实际需要,现在科普又结合着安定团结、和谐社会建设等;第四,科普的体制是中央集权制下的一元化的组织结构。现在到各级科委、科协系统看一下,科普的情况仍然大致如此,这就是传统科普。传统科普在历史上有功劳,但现在过时了,现在要用科学传播来代替传统科普的理念。科学传播并不是要人们完全相信科学,但却要求人们去了解科学,公众在有一定的能力之后,要与科学家来讨论、分享、参与科学;公众某种程度上可以质疑科学。在传统科普的框架内,重视的是知识普及,不太在乎科学的过程和方法,更不在乎科学的负面影响,有些问题根本在科普的框架下无法得到讨论。
恢复博物学实践,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要重视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博物学是这样一种非常古老的、非常“肤浅的”学问,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。现代科学远离了公众,比如说加速器,有回旋加速器、直线加速器等,这些东西都需要甚至百万或上亿元的资金,普通百姓可能连看的机会都没有。不过看也看不懂。普通百姓能够参与实践的恐怕只有博物学,博物学有没有用呢?它对于人们的成长,特别是个体人的成长,是有关的,也是需要的。人的成长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纬度,一是人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动物,有一个社会性的纬度,一个个体与社会、他人的关系,定义了人的一部分本性;二是人作为一个自然人,人是生活在空气里,需要有水、氧气,要进食等等,要与大自然打交道,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好,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,人生也谈不上完美。我们现在说社会化、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,前一个纬度可能比较发达了,但是在后一个纬度上可能不够发达,甚至出现相反发展的情况。
针对“现代性”社会的这种失衡发表,情况也在发生变化。在一些发达国家,博物学又有复兴的迹象,民间组织相当发达,特别与看植物、观鸟、登山等一些户外活动联系在一起。比如英国人喜欢观鸟,有个皇家鸟类学会,是个民间组织,有一百多万会员,计算一下可发现,相当于英国人中每60位公民中就有一位是皇家鸟类学会的会员。观鸟在英国非常流行,我们国家的鸟类手册印五千册,卖了好几年还卖不动,可见国人中观鸟者不多。观鸟可以让人去了解大自然、生态变化,了解鸟的习性,了解另一种动物是怎么生存的。有人会质疑,我们处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,提倡博物学有什么用?当有人挑衅性地提这个问题时,最好的回答就是“没有用”。我们学习任何东西都是为了有用吗?我们人生做很多事情都不是为了用,或者不是为了马上就使用。现在人很着急,我今天投入一百块钱,明天就希望会得到一百二十块钱,如果不升值就好象这个东西就没有用一样。博物学的确有用,我们暂时不提它之用。修炼博物学很难升官发财,百姓修炼博物学也是为了发表论文。就算能认识几千种植物也仍然发表不了一篇论文,为什么呢?现在发现一种新植物物种很难,就算真的发现了,还要做实验,要有DNA的数据,同行专家才认可。百姓看花看草,不是为了写论文,是为了好玩!人这个物种是需要玩的。在玩中,可以不经意了解世界,在玩中也实现人的部分本质。玩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。
我们修炼博物学,去看花、观鸟,在乎的是感受外部世界,在感受的过程中可以提升我们自己,可以有审美的感觉。审美是很难用功用、效用来衡量的。你发现某个东西很美,这很难与别人交流,只有那人同时也看到它很美,俩人才能交流。如果对方根本不喜欢它或不在乎它,就无法交流。修炼博物学是个体自我的一种实现方式,中国近代第一本书《植物学》,是年数学家李善兰与两位传教士合作翻译的,李在书的序言中说:“验器用之精则知工匠之巧;见田野之治则识农夫之勤;察植物之精美微妙,则可见上帝之聪明睿智。”在这里,对于不信基督教的,“上帝”可以等同与“大自然”,也可以等同于“进化”。我们观察、理解大自然,就可以感受到进化的精致,看兰花长成那种形状,就可以感受到进化是多么的神奇、精巧,时间的积累就会产生多么美妙的智慧。“自然神学”般的感受普通人是否可以有?可以!我就感受过,虽然我并不信上帝。
我给大家看几幅图。美洲马兜铃的花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?为了昆虫来传粉,花的喉部为什么长了很多倒刺呢?为了小虫子只能沿着一个方向朝里爬,到了里面之后就会为里面的雌蕊传粉,要一直等到花凋谢以后,口打开了昆虫才能爬出来,再为其它的花朵传粉,这是上百万年进化的结果,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,它很精致。注意我使用了百姓都明白的词语“为了”,上述的叙述也有目的论的嫌疑。但是没关系,我们是在“生活世界”中讲话,不是在“科学世界”中论理。
这是兰花螳螂,我的学生姜虹在西双版纳拍摄的。螳螂的身体部件长得象兰花的花瓣,这是自然选择造就的,它们放在一起给人一种神奇的感觉,好象有某种神灵在操纵一样,这是进化的奥妙之处。百姓仔细观察这些东西,是博物学的实践过程,可以不发表论文,但是可以感受、体验其中的美妙。
这是在我们湖北省美丽的神农架拍摄的某种勾儿茶,小藤条是旋转的,向左旋。勾儿茶属的所有植物都是向左旋的,为什么呢?不知道。问科学家,科学家不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。关于这类“手性”问题,我问过一些植物学专家和物理学家,没人说得清楚。我请教了一位研究植物学的朋友:怎么做才能够在分子层面上来阐述它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手性,他说大概需要两百万人民币,才有可能研究清楚。但是目前科学家的兴趣不在此,因为目前没有用。两百万资金,资本家不会给你,国家也不会给你,所以科学家不研究这个东西。它有意思吗?非常有意思,在农村长大的小孩都会对手性感兴趣,比如豆角是右旋的,金银花是左旋的,紫藤是右旋的而多花紫藤是左旋的,葡萄秧的须子也有复杂的缠绕方向。有没有物种可以同时向左转也可以向右转呢?有!何首乌和微甘菊的同一株藤上茎既可以向左转也可以向右转,为什么?不知道。这些东西都很有趣,普通百姓也会感兴趣,会问为什么?的确不知道。人们很容易想到是不是克里奥里力的引起的,至少现在这种力与它无关,为什么?南半球也有这些类似的植物。黄独是向左转的,紫藤是向右转的,多花紫藤是向左转的,南北半球栽上这些植物,手性不会变。但是,现在克里奥里力跟它没关系,并不等于植物在进化的当初和它没有关系,当年古大陆没有分离的时候,某个地方的古植物在进化过程中是否跟克里奥里力微小的“推动”有关系?不知道。我们能不能做实验呢?我们可以做一个非惯性的转动平台,去测试一下是否能够产生不同的手性,但进化需要相当长的时代,这种检验局限性很大。在分子层面来解析宏观手性的微观调控机理,需要做很复杂的工作,要花大量的钱,而科学家们对些不感兴趣。当然,科学家某些手性问题是感兴趣的,比如杨振宁、李政道对弱相互作用下的手性问题感兴趣,而且获得诺贝尔奖,吴建雄的实验验证了理论结果。在手性催化方面,日本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。在博物的层面,勾儿茶向左转、扁豆向右转之类,科学家没有看到商业价值,还不感兴趣。
在中国,博物学教育在解放前还是受重视的,各级教育中都有博物类的课程,但是现在没有了。最近北大附中在五个年级相继开设了博物学课程,清华附中也在鐧界櫆椋庤兘娌诲ソ鐧界櫆椋庤兘瀹屽叏娌绘剤鍚?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mianzhuzx.com/mzsly/10365.html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