![]() 当前位置: 绵竹市 > 绵竹市美景 > 首届东坡居儋文化思想研讨交流活动论文系列
当前位置: 绵竹市 > 绵竹市美景 > 首届东坡居儋文化思想研讨交流活动论文系列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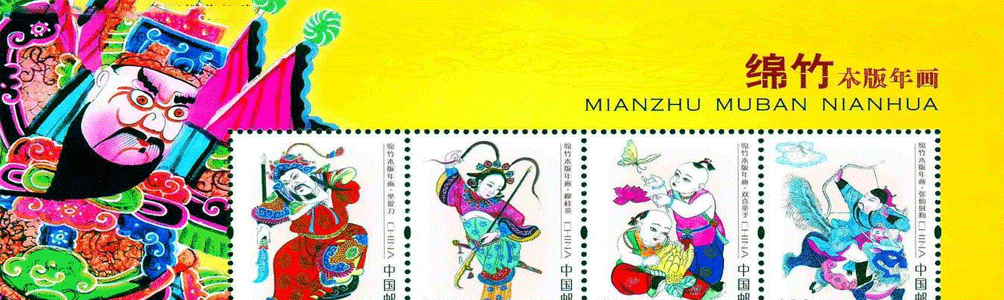
![]() 当前位置: 绵竹市 > 绵竹市美景 > 首届东坡居儋文化思想研讨交流活动论文系列
当前位置: 绵竹市 > 绵竹市美景 > 首届东坡居儋文化思想研讨交流活动论文系列
苏东坡美学思想初探
湖北黄冈涂普生
近年来,随着美学热的兴起,好些同志对我国北宋时期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、少有的全才作家苏轼的美学思想的研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,委实出了不少的研究成果,令人欣慰。在这里,我们想结合苏东坡的一些代表作,采取吟咏鉴赏、追本溯源式的探讨方式,对苏东坡的文理自然就是美的美学思想,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。
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苏东坡的贬谪生活,使他广泛而深刻地了解了当时的社会,了解了社会底层的民众,形成了他一生创作的一个高峰期。在这期间,苏东坡写的佳作,充分显示出艺术美的特殊魅力。应该说,这些佳作是我们研究苏东坡美学思想、观点的极为宝贵的文献。
走进黄州东坡赤壁,人们不仅会被那翠竹红壁、飞檐斗拱、曲径回廊的风景所迷恋,更会被这里珍藏的前《赤壁赋》、《后赤壁赋》和《念奴娇·大江东去》等苏翁词赋所陶醉。赏风景,吟词赋,怡情悦目,美不待言。展现在眼前的仿佛是一幅幅壮丽非凡的画卷:赤壁矾下,江水滔滔,波光鳞鳞,水石咬碰,浪花朵朵。就在这如画江山之上,英豪辈出,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,叫人感奋不已;秋月当空,江水浩渺,一叶扁舟,任泛中流,箫声悠悠,歌声缕缕,潇洒而不失执着,飘逸而不失豪迈,令人超然而乐;冬夜霜露伴寒月,赤壁江山,山高月小,水落石出,主客舍舟探幽,长啸山鸣谷应,孤鹤飞鸣而入梦境,虚幻而不失真实,孤寞凄凉而不失进取、抗争,使人如临其境,和苏东坡喜怒哀乐相共……反复吟诵苏东坡的前《赤壁赋》、《后赤壁赋》,我们所陶醉的是:自然美;我们所钦佩的是:苏翁笔下自然美。来到惠州和儋州,吟诵《食槟榔》、《雨后行菜圃》,那诗中描写的南国风情,田园乐趣,怡然自乐的情怀,跃然纸上。我们所陶醉的,也是自然美;我们所钦佩的,也是苏翁笔下的自然美。这些诗赋显示出了苏轼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——文理自然就是美。
文理自然就是美这种美学思想,早在陆机《文赋》和刘勰《文心雕龙》里,就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。陆机说:“期穷形而尽相。”刘勰说:“体物为妙,功在密附。写气图貌,既随物以宛转,屈采附声,亦与心而徘徊。”到了苏轼手里,更明白地肯定为一种美学思想,并在文艺创作实践中加以运用,苏东坡在《答谢民师书》中明确地说:“文理自然”,“如行云流水”,才不矫揉造作,使作家的真情实感随着自然而流露,创造出的艺术品才能给人以自然美的感染。他主张,文艺创作应如“风行水上,自然成文”。只有使作品浑然天成,无斧凿痕迹,作家、作者的真情实感才能自然流露,收到“意之所到,则笔力曲折,无不尽意”(《春渚记闻》),作品潇洒自如、超然不拘的艺术效果。苏东坡也常常以“文理自然”为自豪。他在《自评文》中津津乐道:“吾文如万斛泉源,不择地皆可出,在平地滔滔汩汩,虽一日千里无难,及其与山石曲折,随物赋形,而不可知也。”苏东坡在评论吴道子的画时,也阐述了文理自然就是美的美学思想。他在《书吴道子画后》中说:“道子画人物如灯取影,逆来顺往,旁见侧出,横竖平直,各相乘除,得自然之数,不差毫末,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……盖古今一人而已。”苏东坡这些论述,生动而又形象地说明,文艺创作不是矫揉造作,它是生活的艺术再现,只有文理自然,才能给人以自然美感。而大自然本身的美是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,给人的美感也是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。只有“文理自然”,才能使作品达到“天成”、“自得”、“超然”的艺术效果(苏轼:《书黄子思诗集后》)。可见,“文理自然”就是美,是苏东坡重要的美学思想。他的这种思想贯穿于他在黄州、惠州的整个创作过程,苏东坡的黄州东坡赤壁词赋和惠州儋州的田园诗歌,便是有力的例证。
苏东坡“文理自然”的美学思想,是比较成熟,比较系统的。
首先,苏东坡从“文理自然”这个美学思想出发,认为,文艺创作者要深入生活,目见耳闻,得自然之数,才能做到“文理自然”。事不躬亲,一意臆造,是不能得到自然之数,求到精妙,抒发真情实感的。这样的文艺作品,“则其不为人之所呕弃者寡矣。”(苏轼:《盐官大悲观记》)更谈不上给人以自然美的享受。据记载,苏东坡获赦自儋州北返,路经一州。当时这个州刚建好了一座石桥。郡守拿出纸笔,请苏东坡为石桥撰文,苏东坡谢绝,道:“轼未到桥所,难以想象落笔。”(见《容斋三笔》)苏东坡是元丰三年(公元l年)二月一日到黄州来的。他虽然常去赤壁矶上游览,但由于没有月夜泛舟赤壁矶下的生活,未得自然之数,所以在黄州住了两年,没有写《赤壁赋》。只是在元丰五年(公元l年)农历七月十六日,苏东坡同来黄州看他的绵竹武都山道士杨士昌等人一道,乘着月色,泛舟赤壁之后,才写出了前《赤壁赋》;后来,十月十五日,他又带着两个客人,月夜攀登赤壁矶头,泛舟江面。复写出《后赤壁赋》。据说,苏东坡为了弄清楚农历七月十五日月亮出山时的位置,竞在赤壁观察过好几次,最后才写出了“月出于东山之上,徘徊于斗牛之间”的句子来。这些说明,苏东坡是恪守“文理自然”这一美学思想的,他没有熟悉的生活,未得自然之数,是决不会轻易动笔的。
也是从“文理自然”这一美学思想出发,苏东坡还强调,文艺创作必须追求艺术的真实。苏东坡主张,文艺创作追求“文理自然”,当然要努力做到“穷形尽相”,“随物赋形”。这是毫无疑义的。他在《文与可飞白赞》中高兴地说道:“美哉多乎;其尽万物之态也!”但是,光做到这一点还不叫艺术真实。艺术的真实,必须是既要“形似”,更要“神似”,并且熔真实情感于形神兼备之中。要做到这一点,文艺创作者要把着力点放在“得自然之数”,亦即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上。一方面,苏东坡主张“如以灯取影”,“得自然之数,不差毫末”。(《书吴道子画后》)强调“形似”;一方面,苏轼又指出“论画以形似,见与儿童邻”,“画马不独画马皮。”(《韩干三马》)统观起来,这并不矛盾,苏东坡是主张既要掌握“不差毫末”的“数”,达到“形似”;更要掌握能出奇妙的“精”,达到“神似”。最后给人以“形神兼备”的美感。他在《与何浩然》的信中说:“写真奇绝,见者皆言十分形神,甚夺真也。非故人倍常用意,何以及此,感服之至。”说的就是这么个意思。“形神兼备”,就是事物的本质特征的外露与内涵,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,就有可能发掘生活之理,自然之理,“有见于中”,“而发于咏叹”。这样,文艺创作者的真情实感就能产生,并托物寄情,自然奔放。苏东坡在前《赤壁赋》中描写他们泛舟赤壁之下的情景,是这样写的:“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。浩浩乎如凭虚御风,而不知其所止,飘飘乎如遗世独立,羽化而登仙。”描写依歌而和洞箫的声音是:“其声呜呜然,如怨,如慕,如泣,如诉,余音袅袅,不绝如缕,舞幽壑之潜蛟,泣孤舟之嫠妇。”在《后赤壁赋》中描写寒月霜露下的赤壁江面是:“江流有声,断岸千尺,山高月小,水落石出。”这些描写,可谓形神兼备了,收到了“诗缘情而绮靡,赋体物而浏亮”(《文赋》)的艺术效果。诗情画意,情景交融:使人如亲临其境,感觉到了彼时彼刻苏轼脉搏跳动的频率。前《赤壁赋》中也有不小的篇幅说理谈玄,但都富有形象和韵味;《后赤壁赋》通过对赤壁江山萧条冷寞景象的描写,生动地、形象地表达了苏东坡进取、抗争的精神。真情实感,感人肺腑。称得上是“神与万物交,其智与百工通”。总之,苏东坡抓住自然界的一事一物的本质特征,获取了形神兼备的艺术真实;又以艺术真实,再现了自然界中存在的自然美,创造了“文理自然”之美,可谓匠心独具,至情至文,出神入化了。苏东坡在惠州写的《雨后行菜圃》,既写了“霜根一繁滋,风叶渐俯仰”的雨后菜圃景象,又写出雨后行菜圃者“未任筐营载,已作杯盘想”的喜悦心情。有形有神,同样使人感受到文理自然之美。苏东坡曾赞扬韩干画的马是“画马不独画皮,画出三马腹中事,……”(《韩干三马》)其实他自己写诗、填词、作赋也是这样,模范地实践了自己的美学思想。
苏东坡主张“文理自然”就是美,还有一点需要说及的是,他执着地主张潇洒自如,自然成文,否则就达不到“文理自然”的艺术境界。他常常自誉道:“吾文如万斛泉源……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不可不止,如是而已矣”。这里告诉人们,文艺创作要根据所表现的对象的自身状态、特征、规律,自然地进行描绘,不可人云亦云,千人一律,恪守陈规陋习。要敢于创立自己的、符合自然的风格和流派。正是他,为了创作“文理自然”的艺术作品,在词作方面,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,摆脱绸缪宛转之度”,“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”,“独树一帜,不域于世。”为了做到“文理自然”,他在当时的词坛上剁了“三板斧”:其一,开豪放派词之先宗。珍藏在东坡赤壁的《念奴娇·大江东去》(一作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),便是苏东坡豪放派词的代表作。由于开了豪放派词之先宗,使得东坡词无论在北宋,还是在整个词的发展史上,都称得上是一座高峰。《念奴娇·大江东去》,是苏东坡于元丰五年(公元l年),也就是他被贬到黄州的第三年七月写的。当时,他屹立在乱石穿空、惊涛拍岸的赤鼻矶上,由“赤鼻”联想到“赤壁”,又由“赤壁”联想到赤壁之战,思情万千,不可遏止,遂乘着酒兴填写并草书这首词。格调豪放,气势磅礴,只有关西大汉唱最好。苏东坡亦引其豪放词为自豪,曾不止一次地说:“虽无柳七郎风味,亦自是一家,呵呵。”豪放派词,较能体现苏东坡的艺术个性特点,终于另辟蹊径,“指出向上一路,新天下耳目。”(《碧鸡漫志》)他之所以喜豪放,弃婉约,盖由于豪放利于“文理自然”。其二,冲破声律束缚,“不喜剪裁以就声律。”读其词、赋,确实感到一气呵成,浑然天成的雄浑的自然美。《念奴娇·大江东去》便是一例。他在这首词里,着重抒发胸中之壮志,发表自己对人生的看法。所以不愿以律害意,“间有不入腔处”。苏东坡本来是通音乐,会唱曲的,可偏偏存在这么个“毛病”,何故?原因就是:“但豪放,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”(《历代诗余》)。他认为,这样不以律害意,更利于达到“文理自然”的艺术美的境界。其三,主张“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(《书吴道子画后》),熔议论、抒情、写景于一炉。当描写的就要描写;当抒情的就抒情;当发议论就发议论。也是为了“文理自然”这一艺术美的创造。在《前赤壁赋》中,他以主客对话的形式,大段大段地发表议论,揭示了重要的人生哲理,在《后赤壁赋》中,也有一些议论;在《念奴娇·大江东去》中,以议论为全词作结。在惠州写的《和陶归园田居六首》、《食槟榔》、《食荔枝二首》等也是将写景、抒情、议论熔于一炉的。苏东坡反对“游谈以为高,枝词以为观美者”的空泛议论,主张艺术作品要表现“理趣”,以景寄情,以情景而自然生发议论,形成理趣。使“理”既有根系、须眉,又有情趣。这样,创作出的文艺作品就能给人以“文理自然”的美的享受。我们读东坡赤壁珍藏的苏翁词赋和惠州诗歌,往往被其中的“理趣”而深深打动。觉得他叙事自然,绘景自然,抒情自然,说理也很自然,这正是苏东坡的“文理自然”就是美的美学思想所放射出的光华。苏东坡在当时文坛上,特别是词坛上连砍“三板斧”,而且砍出了一条新的路——向上之路,无论是从那个角度上说都是颇不容易的。他的作为,他的建树,足见一种一经确立的美学思想——“文理自然”就是美,支配力量是何等的大,产生的成效是何等的卓著。珍藏在黄州东坡赤壁的前《赤壁赋》、《后赤壁赋》也好,《念奴娇·大江东去》、《满庭芳·归去来兮》、《浣溪纱·休将白发唱黄鸡》、《临江仙·夜归临皋》也好,以及在惠州写的《和陶归园田居六首》、《撷菜》、《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》也好,都闪烁着“文理自然”就是美这一美学思想的光芒。换而言之,都是实践“文理自然”就是美这一美学思想的产物。苏东坡的这一美学思想,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,他强调了“自然”的存在是客观的,是“文理”的基础;“文理”是客体自然的自然流露和反映,文发乎自然,理寓于自然,文理畅乎自然,给人以自然美。这种美学思想是很值得借鉴的。对于那些以想当然,随意编造,甚至迎合低级趣味为美者,实在可作为一面镜子。
苏东坡的美学思想是一种富有积极奋起精神的美学思想,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,反映了主、客观的有机结合的创作途径。是属于开拓型的。它既要求作家、作者按照客观事物本质特征能动地、维妙维肖地反映客观事物;又要求作家、作者不要拘泥于客观事物形体状态的刻画,而要超乎客观存在,发出自己的心声,揭示出符合自然的“理”,以晓天下。这是苏东坡对我国美学的一大贡献。今天,我们研究学习和借鉴苏东坡的这一美学思想,无疑是十分有益、十分必要的。
已完结,敬请期待下一篇!
海南省儋州文化研究会官方平台
联系方式:
-
传直:-
邮箱:dzwh
.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mianzhuzx.com/mzsmj/14529.html



